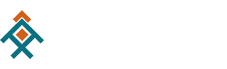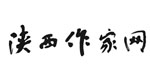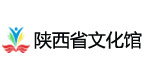发布单位:长安区图书馆
发布单位:长安区图书馆
 发布时间:2021-11-26
发布时间:2021-11-26
《掠过终南山北麓的风:长安作家文集》是由西安市长安区图书馆主编,共收录长安籍作家和非长安籍而在长安工作生活的109位作家作品汇集而成,全面且系统地提供长安作家及他们的作品情况。这是长安文学队伍的一次大展示,也是对长安已故文学前辈的缅怀,同时是新老作家以及社会对长安文学作者的了解、学习、交流的资料库。
书香润泽心灵,佳作启迪人生。为了使大家更好的了解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长安作家文学成绩和成果,深刻感受长安历史文脉和文化特征。从2021年9月1日起长安区图书馆将每周推送3篇长安作家文集作品,以飨读者。
蒲 扇
作者:刘英雄
夏天到了,想买一把蒲扇,找了许多家杂货店竟然没有,很是失望。想不到原先到夏天杂货店里成堆卖,家家都会有几把的所谓柯榻叶子,现在倒成了稀罕东西。想想也是,现在居家电风扇早已成了从城市向农村撤退的散兵游勇,空调对普通人家都已是平常物件。再热的天气,躺在床上就那么拿起遥控器一按,嗖嗖的凉风就吹过来了,要多滋润有多滋润,谁还用摇那个破扇子? 即使那个杂货店进上几把蒲扇,卖给谁呀?还不最后当柴火烧了。
过去年代的夏天,蒲扇可绝对是个重要东西。印象最深的,是妈从地里割麦回来,放下镰刀就带着一身汗水急忙进灶房做饭。做饭烧的是麦笕,火挺大,长长的火焰扑出灶膛,整个灶房像个大火炉。妈要烧锅,还要擀面、炒菜,浑身的老汗水新汗水像道道小溪一样地往下流。一会儿,全身的衣服都贴在了身上,连布鞋的帮子都叫汗湿透了。终于,一锅连汤面做好了,妈把面舀进一个大盆,端出灶房,又拿来碗筷舀好凉着,这时她才能歇一会儿。这时候妈最惬意的,莫过于坐在小板凳上,一面解开汗水浸透的衣服,一面很快地摇一把蒲扇。出过许多汗的身子在蒲扇一下一下的风里,每个汗孔都极度地舒张,简直舒服极了。有时候,看着妈太热,我们就换着给妈扇扇子,双手握着扇子使劲上下扇着,恨不得把全世界所有的风都扇出来使妈凉快。这时候是妈最舒心的,不但有身上的凉爽,还有心里的宽慰。
吃饭也太热了。热乎乎的汤面碗烫得端不到手上,端起来一大碗热汤对着脸,没吃汗都会流个不停。饭是旗花汤面片,一个手端碗,嘴一下一下地喝着,一个手拿一把蒲扇,一下一下地扇着。即使这样,一碗饭吃完,也许出的汗比喝进去的汤还多。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就实行互助吃饭,互助扇扇: 一个人先吃,一个人给扇着扇子。当然每当这样换工时,每个吃饭的人都尽量吃得慢。为了公平,我们看着表限制吃饭时间,并且规定扇扇子要扇出的是悠悠风,小风,还是大风,或者狂风。
暴热的白天终于在太阳落了以后不那么晒了,但地面上、房屋上、收割回来的麦子上吸收的热气依然使所有的东西都热烘烘的。炕沿子是热的,炕席是热的,根本就没法睡觉。小小的一间厦子房,坐东面西,白天晒了一天,成了个烘炉。脚地还有一点儿凉气,妈把席子拉下来铺在地上,地上铺得满满当当的。玩了一天,我们都乏了,小孩子再热都能睡下。在我们睡下后,妈并没有睡,就那么坐在席子上不停地给我们扇着凉。过一会儿,把一个个翻一翻身,看着席子上汗湿拓下的印子,妈就更是不睡了。蚊子嗡嗡地落在我们的脸上,手一拍人也跟着坐了起来,挠着被蚊子咬的疙瘩,嘴里说着含混不清的梦话。没说完,眼没睁地倒头又睡。迷迷糊糊地,感到妈坐着打盹,手里的扇子还在有一下没一下地机械地摇着。
一把蒲扇一毛一分钱,挺贵的,因此一把扇子要用很多年。为了使扇子耐用,买回后要用一寸宽结实的咔叽布条给扇子包个边。有些爱好的妇女,包边时用两寸宽的布条,留出一寸剪成牙状,不但好看,扇起来风也大了许多。
妈用了多年的蒲扇还在老家的墙上挂着。扇把被汗手握得光滑发亮,扇面上也浸透了汗水,颜色深沉,掂着沉甸甸的。蒲叶多处已经破了,由于有用蓝色咔叽布包的边,扇子并没有散开,但有些地方的包边已经磨烂了。看着这油汗的扇子,看着扇子上的每一个破口,似乎还能感到那曾经的凉意和竹席上的永远也做不完的睡梦。如今扇子上落满了厚厚的灰尘,预示妈走的时日已多。三年前,辛劳一生的妈终于也像这把蒲扇一样,永远地休息了。
蒲扇是一段长长的老百姓的夏天。
来 子
作者:刘英雄
又到过年了,想起了来子。
来子姓啥大名叫啥没有人知道,但这无所谓,一点儿也不重要,几十年来郭杜的人老几辈子,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公社书记是谁,却不会不知道来子。
来子是个杀猪的。
来子是康杜村人,康杜村人大多姓康。想来来子也应该姓康, 其实姓康不姓康的对来子真的是无所谓的,反正村里人互相叫着从不带姓,带着姓叫是叫外来人的。而对来子,凭着杀猪手艺,哪怕是姓个老鼠麻雀,也是足以威震四方的。
七零年前后几年是来子最威风八面的时候。那时来子三十岁左右,墩墩个儿,四肢短而粗壮,手大脚大,黑脸膛,五官大而分明,那时候人们还不知道秦始皇兵马俑,现在想起来一对比,其实来子最像的,那地坑里的将军俑。来子厚厚的上嘴唇上,长了一颗黑豆样的痣,简直就像明山好水相衔接处的亭子,给这张脸上增加了不少神韵,且形成焦点,有那么点儿孔武,有那么点儿霸气,有那么点儿憨厚,有那么点儿呆痴。然,看得多了,也许还能看出点儿怪异呢。
起码全公社的猪都归来子杀。
每年杀猪分两个时节。一次是阴历的六七月间,郭杜各村过古会,几乎隔几天就有一个村子杀猪,这样杀,来子不用忙,可以从容不迫地杀了一村又一村。 还有一次是腊月的二十五以后,这时比较集中,来子几乎是一个村一个村的赶场子,几天几夜不停刀, 忙虽然忙些,但能挣些钱和落一大堆猪尾巴过个好年,来子的精力这时候反倒格外的好。
该杀过年猪了,各个村子要先派人跟来子定日子,到了时候,来子自然就会右胳臂肘挂着那个已被猪血猪油手汗污泥涂抹得脏兮兮的大竹担笼来的,担笼里面放着沉甸甸的杀猪家伙: 细而长的闪着寒光的捅刀,宽而短的沾着猪血碎骨的砍刀,刮毛的刨子,挂肉的钩子,捅条,细麻绳,当然了,还有一块磨石。来子很守时,说啥时候到就啥时候到,虽然那时候来子不知道时间就是金钱这样的名言,但来子想着不能耽误乡党们过年吃肉,来子心里放着乡党呢。村里要在来子到来之前,叫人烧上几锅开水,这样来子到后就不会耽误时间。
来子人实诚,一到接过村里管事的递过的纸烟,点着火咂在嘴上,马上就与帮忙的小伙子去圈里逮猪。该挨刀的猪虽然吃得比平时好了,但也许一代一代已经遗传了某些预感,特别爱哼哼,真应了那句“肥猪哼哼挨刀呀”。生人一进圈,猪要么左冲右突,乱窜乱跑,要么屁股顶在一个墙角,长嘴獠牙凶狠地盯着每一个靠近的人。这时人多了没有用,就要看来子了。在众人乱扑乱撵时,来子始终不动声色,黑黑的脸上没有赞许,也没有阻止,嘴半抿半张,整齐的白牙微露着,也许还给猪一个可信赖的笑脸呢,猪在惊恐之中,感觉到这是一个好人,希望得到这个人的保护。来子不紧不慢地靠近猪,一副和事佬的样子,深得猪的好感。猪彻底地放松了警惕。来子的挠痒使猪感到舒服,它甚至想躺下来,是不是还想唱点儿猪戏也说不准,真应了那句“跟猪一样,记吃不记打的货”。其实,也就在猪眯缝眼的一会儿,来子的一只手就已像铁钳子一样地攥住了猪的耳朵。就是这么一只手,偌大的一只猪立马被提起来,此时不管这头猪有多肥多大,也就只有鬼哭狼嚎后悔莫及的份了。
猪被拉到那只不知有多少同类虽拼命抗争但最终难逃被宰杀命运的结实榆木大板凳上,一时叫声响彻村子,招来了许多看热闹的人。尽管西北风呼呼地吹着,也许还飘着雪花,但猪的嚎叫,大锅开水冒着热气,压猪的小伙子害怕而又兴奋的脸,来子不紧不慢的操刀,看热闹的人叫声喊声,把个场面烘托得热烈而富有生气。
猪一直叫着,也许时间长了,也许叫得没劲了,也许又觉得没危险了,叫声渐渐地趋于平缓,节奏长而均匀,猪又把眼睛眯缝上了,平平的板凳躺着怪舒服的,比疙疙瘩瘩的猪窝里强多了,舒服一时算一时,猪才不管别人有啥想法呢。
猪睡得正舒服,来子用左手轻轻地在猪脖子下扑梭了几下,猪本能地把脖子伸的更长了。来子右手拿着刀,用刀尖在猪脖子上一比画,猪眯缝的眼睛倦倦地睁了一下,又懒洋洋地合上了,并无什么反应, 也许猪看见了刀,也许没看见,反正它懒得去想,雪还在不紧不慢地飘着,风还在不紧不慢地吹着,就在这种懒洋洋的气氛里,看热闹的人知道要发生什么,嘈杂的人声静了下来。也许就在人们屏息静气的瞬间,随着一道白光无声地一闪而逝,猪的叫声突然尖利地刺破阴霾满天的空气,急促地刺激着村子的每个角落。猪拼命地蹬着四蹄,企图挣脱,再看来子手上那把差不多有两尺长的刀,只留了半截木把楔在猪脖子上,似乎那里有一个洞,给用木塞子塞着。猪还在残忍而剧烈地叫着,来子感到刀已刺入猪心,就叫在一旁早已等候好的人把一只放了点盐的洋瓷盆子端着接在猪脖子下,随着刀的抽出,一股血瀑喷涌而来,哗哗地在盆中汇成一个血潭,上面泛着血沫,一会儿,血流越来越小,最后变成迟滞的滴答。这时看来子手里的刀,已成了一个红红的血板子,也许只有此时此地,是体会“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最佳境界。
猪死了,来子把在血里泡过的大手在猪毛上擦了擦,指挥着打下手的人把猪抬进有半锅开水的巨大铁锅里,一人拉尾巴,一人拉耳朵,来回地在水里荡着。一会儿,再翻过来。这时的猪在水里是那么安详,没有了嚎叫,没有了挣扎,甚至连纹丝的不安都没有,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眼睛微闭,四肢长伸,“死猪不怕开水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要忘我和豁达的,要做到这一点,也只有猪了。
猪又被抬上大板凳,来子拿刀在猪的四蹄小腿处割一个小口,用一根指头粗的捅条由口子插入,四下里捅一捅,然后来子用嘴咬住口子,一下一下地吹起气来,一会儿,眼看着猪胀大起来,这时有人用挠钩把不断地在猪身上捶打,猪很快就滚瓜溜圆得像个气球一样飘搁在板凳上了。
看着吹猪有意思,打下手的小伙子一个一个的也想吹一吹,结果几个人把脸努得通红,脖子上青筋暴得多高的,一点儿气也吹不进。“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来子吹牛不敢说,猪可是实实在在地吹了起来,到底不是一般人。凭这一点,来子就应该威风八面,就应该受到崇拜,就应该受到前呼后拥。
吹圆了的猪身上没刮干净的毛丝丝可见,来子会用杀猪刀像剃头一样地再刮一遍,刮完用清水冲干净,然后把猪后小腿关节的连筋割断,将小腿折成T形,倒挂在早已搭好的架子上。先把猪尾巴连着根部的一坨子肉旋下来,放在担笼里,这是给来子的份子,是杀猪行的规矩,下来就该开膛了。来子先用刀轻轻地由尾巴处沿着猪肚子向下划一条浅口,直到脖子,然后再次割透腹腔,但只能割至肚子中间,这时肠子会流出来,马上就有人端来一个筛子,稀里哗啦地立时就咕涌涌地流得满满当当。
猪膛里冒着热气,切口齐齐的,皮、肥膘、瘦肉、板油,一层一层清清楚楚红红白白,极像地质图上的地壳结构。
趁着热气,来子极快地用刀割下一块板油,手一扬,往嘴里一放,“哧溜”一声吸入肚中,看起来极滑溜极有味的样子。打下手的人和看热闹的,也想饱一下口福,也学着来子拿一块板油往嘴里一“哧溜”,虽然很张扬地说好得很好得很,但谁都看出他们肚子里的难受。
分肉也有究竟。
因长期缺油水,人人都喜欢膘厚的,若能有一拃厚的膘,是最受欢迎的。肥膘多,用肥膘炸点儿油,炒菜就有油了,而且肥肉切成肉丁做臊子,肉肥汤汪。
肥肉人人爱,尤其在过年时,乡党们讲究“冬吃槽头”。槽头肉特别肥,虽然是个血脖子,但并不影响人们对油水的追求。对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拔拌,即抓阄,谁抓到几号是几号,按次序从脖子分起,天公地道。
来子割肉,不偏不倚,一刀下去,上下宽窄绝对一样,乡党的说法是: “来子如果当官,绝对是个包公。”
村子大的,过年要杀几头猪,来子照样不慌不忙,先一气杀倒两个,然后指挥打下手的一个锅里放两只同时烫猪拔毛。看热闹的人看来子连着杀猪,有如用指甲盖挤虱子一样从容,一样潇洒,颇为着迷。
来子杀猪时他爸会跟着给帮忙,老汉是个干瘦老头,没有来子的那副大骨架。老汉除了给来子递刀递钩外,有时还在关键地方指点一下,应当也是杀猪的。如确是这样,来子的娴熟手艺就应该是家传了,不知是否他家的门楼上有“耕屠传家”字样?
来子现在也应该有六十岁出头了,不知还杀不杀猪? 儿子有没有继承? 也许,哪天碰上个谁家过事自己养猪杀肉,若有一个敦实老人给杀猪的小伙儿递家伙,那可能就是来子。
委屈的英雄笔
作者:刘牧之
我二哥出生的那年,我父亲还在咸阳教书。五一劳动节前夕,父亲被单位评为先进教师,奖品是一支上海产的英雄牌钢笔。据父亲说,那支英雄笔在省城西安东大街的文具商店里标价是九元钱。20世纪 60年代初期的工资水平很低,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是三十几元。我父亲当时一个月挣四十块零两角钱。每月回家,父亲给我母亲5元,再给我奶奶5元,这基本上就够她们30天的零花了。由此可想而知,在那个年代,如果走在大街上,偶尔看见谁在挺起的胸口上神气地别着一支英雄笔,就觉得那人特别体面。这是一种荣耀身份的象征,绝对令人艳羡不已。
月底,父亲回到莎镇,一脚刚踏进老宅院,手上的包还没有放到地上,就急不可耐地从口袋里掏出那支黑色的英雄笔,兴奋地举在我母亲的眼前夸耀。我母亲是我们莎镇最早接受教育的那一批女子,看见这支英雄牌钢笔,眼睛顿时一亮,立即就喜欢上了。我母亲一把夺过来,爱不释手地说,以后我就用它给你写信! 我姐姐当时14岁,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在旁边看见了,心里也想要,但是不敢开口。
吃过晚饭,一家人正兴致勃勃地轮流拿着笔爬在堂屋子中间的那个黑色核桃木的大方桌上试笔、写字,我那出嫁不久的二姑回娘家串门来了。我姑父家和我们家紧挨着。我父亲和我二姑兄妹两个的感情很好,我二姑和我母亲姑嫂两个的关系相处得也一直很融洽,一些亲密的私房话,二姑也只给我母亲悄悄说。我二姑从小就喜欢看书,尤其是小说,我父亲每次从咸阳回到莎镇,都要给她捎回几本,«呼啸山庄»«包法利夫人»«牛虻»什么的,源源不断。所以每次我父亲回到家,她就会在第一时间跑过来看哥哥又给她捎回来了什么好看的小说。 二姑进门看见我父亲趴在桌子上用一支新钢笔在纸上试着写字,就好奇地说,咦,这么好看的一支笔,哥,叫我看看! 我父亲随手把笔递给她。大家把头挤在一起看二姑侧着脸认真地写字,都夸她的柳体楷书写得好。大家在一起说笑,其乐融融。
星期天下午我父亲要去咸阳上班了,已经到了车站准备上车时,忽然想起那只钢笔了,摸遍浑身的口袋却怎么也找不着。父亲心想,可能还在桌上放着呢。也就没有上心。
第二个月末,我父亲再次回到莎镇,还是没找见那支钢笔,于是问我母亲,我母亲说她没拿。一时着了急,又问我姐姐。我姐姐说她也没拿。正说着,二姑来了,二姑说她也没拿。母亲想,这一个月来,家里也没来什么生人,便有点儿闷闷不乐。我父亲直到第二天临走时,还是没有问出来到底谁把他心爱的钢笔拿走了。父亲想,最有可能拿笔的三个人,都是自己最亲爱的家人,不管是谁拿了,都没啥。肉烂了,还在锅里呢,于是再三叮嘱我母亲,从此不要在我二姑跟前再提起那支钢笔。于是若无其事地走了。
这本是一件很正常的家庭矛盾,父亲万万没有料到,因为自己的这支笔,我母亲和我二姑两个人从此心里有了嫌隙。
我母亲首先不乐意了,觉得这么好的一支笔丢了,怪可惜的,挺心疼。于是就怀疑是我二姑拿了。我二姑开始以为我母亲不愿意我父亲把笔给她,故意说笔丢了。后来感觉自己又被亲爱的嫂子怀疑,心里更加憋屈。二姑想,别说我没拿,就是我把哥哥的东西拿了,我也是理所当然,光明正大!
姑嫂两个心里闹起别扭,就开始互相怀疑起来,关系渐渐不和睦了。但是因为我奶奶的家教严格,她们两个面和心不和,心里再起矛盾,表面上一时还不敢明枪仗火地表露出来。
我二姑心里觉得冤屈,郁闷,就想伺机专门发泄一下。
那几年生产队发展养猪事业,要求家家户户都养猪,如果不养,就不给分口粮。我们家里人口多,粮食常常不够吃。两个孩子还小,我母亲忙不过来,不敢养大猪,快开春时,就在镇上买了一个小猪娃,用绳子拴在院子里的柿子树上。这样一来,队上再分粮分菜什么的,我们家就也有一份。
猪娃渐渐长大了,我母亲就想在猪圈里给小猪盖一间小房子。但是家里没有瓦,不久前我二姑刚拆了自己南边的小厦房,几百页小瓦堆放在院子的墙根下边,很占地方。二姑就说,二嫂,把这瓦给你,盖猪圈房子去,你用上。我母亲就和我姐姐欢欢喜喜地去她家里搬了120页小瓦。
很快冬天到了,天冷得人不敢伸手。这天下雪了,还刮着西北风。雪还没停住,二姑便过来给我母亲说,她公公想盘一个土窖,冬天里好存放萝卜、白菜、红薯什么的,要用瓦呢。二姑要我母亲立即把那些瓦给她还了。我母亲一愣,随机说,那就等天晴了给你还,行不行? 我姑平静着脸说不行,非要当天就给她把瓦还了!
我二姑跟我母亲打的,其实是一场心理战。
我母亲正好在我二哥的月子里。我母亲婚后第一个孩子都没留着,就把自己三妹的小女儿抱养过来了。也就是说,从血缘上讲,我姐姐其实是我表姐。我姑就暗自想着,我大哥在家是宝贝蛋子,并且年龄还小,天寒地冻的,我母亲绝对不会叫他去搬,而且自己也不忍心让亲侄子受罪。二姑于是判断我母亲只能叫我姐去搬那些瓦。这样一来,她就能很巧妙地把自己半年来对嫂子的怨愤发泄了。
当时我们家里没有劳力,不管家里家外,做活儿全凭我姐。吃水都是我大哥和我姐抬着往回走。我姑的意图很明显,我母亲一眼就把它识破了。我母亲于是将计就计,故意没有叫我姐去搬。我母亲心说,我女儿大冬天的给你还瓦,我肯定心疼,你当然不心疼。但是我儿子是我的宝贝疙瘩,也是你的宝贝疙瘩,那是你娘家的亲侄儿呀。我虽然心疼俺娃,但是对你而言,你肯定也一样的心疼。我也狠下心,看最后到底是谁报复谁! 我母亲将计就计,反而要将二姑一军。于是很干脆地说,你要了,就给你还嘛。
外边毕竟是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冰冻三尺啊。我母亲于心不忍,于是给我大哥浑身上下穿得暖暖的,胳膊上套了一对蓝套袖,两手还戴上一双厚手套,脚上蹬上棉鞋,并把自己的围 腰围在我大哥的胸前。我母亲看着被她全副武装起来的儿子,交代说,你一次搬上10页,转个半圈儿,搬上12个来回,也就搬完了。
我姐和我大哥顶风冒雪把刚盖起来的猪房拆了。我大哥独自一人在雪地里往返于我家和二姑家之间,猫着腰来回奋力搬瓦。他一次只能搬起10页瓦。20个来回搬完了,我母亲对我大哥说,你去给你姑说,就说你把瓦搬完了,叫她数一下。
我大哥于是满脸潮红,头发里冒着热气,走进我姑屋里,看着二姑的脸认真地说,姑,我给你把瓦搬来了。一共120页,你把那数一下。
其实我大哥在雪地里搬瓦期间,我姑一直忐忑不安地躲在自己的厦房里。她听见院子的脚步声和摞瓦的声音,一直没好意思出来看, 她原以为在外边摆瓦的是我姐姐,心里一直暗自得意。这会儿忽然看见我大哥浑身是土脏兮兮地站在她的跟前,两只小手冻得跟胡萝卜一样,一下子就愣呆了!
我二姑的计谋彻底失败了。
我二姑赶紧蹲下身子,不由自主地攥住我大哥冰凉的小手,紧紧贴在自己的面颊上,两股眼泪却忍不住从面颊流了下来。我姑哭泣着,喃喃地对我大哥说,那笔我真的没拿,你妈把姑冤枉了!
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都扫房、祭灶。我母亲和父亲奋力抬起那张从先祖传下来的笨重的核桃木大黑方桌,将它小心地移到了北面的土墙下。忽然,我母亲不经意间低头看见,砖缝里,静静躺着一支黑色的泛着美丽金属光泽的英雄牌钢笔……